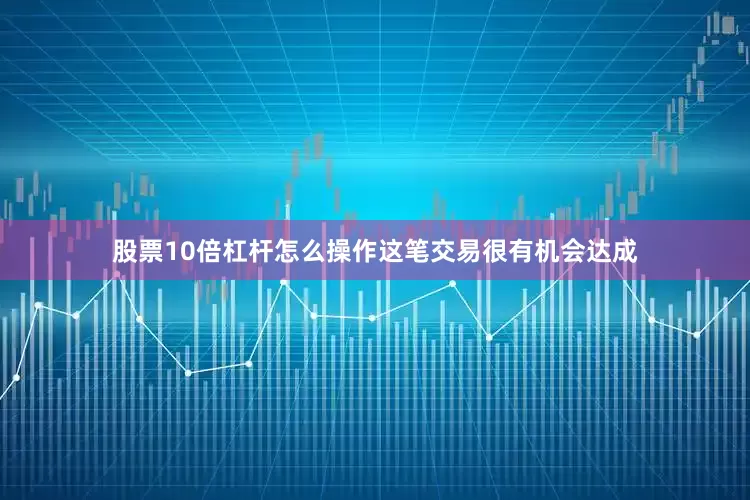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罗一茜
陈年喜曾是一名矿山爆破手。用风钻机打出洞,再将炸药抵进深处,点燃引信,起爆,这样的工作他干过16年。
同时,他还是一名诗人。平时,他会在用完的炸药箱纸板上写诗,刻意不让身边人知道。他写诗的动机很简单,因为这让他“感觉自己活着”。
2015年的一场颈椎手术终结了他的矿工生涯,却开启了另一段人生。离开矿山后,陈年喜将积蓄多年的生活体验倾注于文字,《炸裂志》《微尘》等作品相继问世。评论家称赞其作品“重振了《诗经》的民间叙事传统”,以苍凉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劳动者悲怆而炽烈的生命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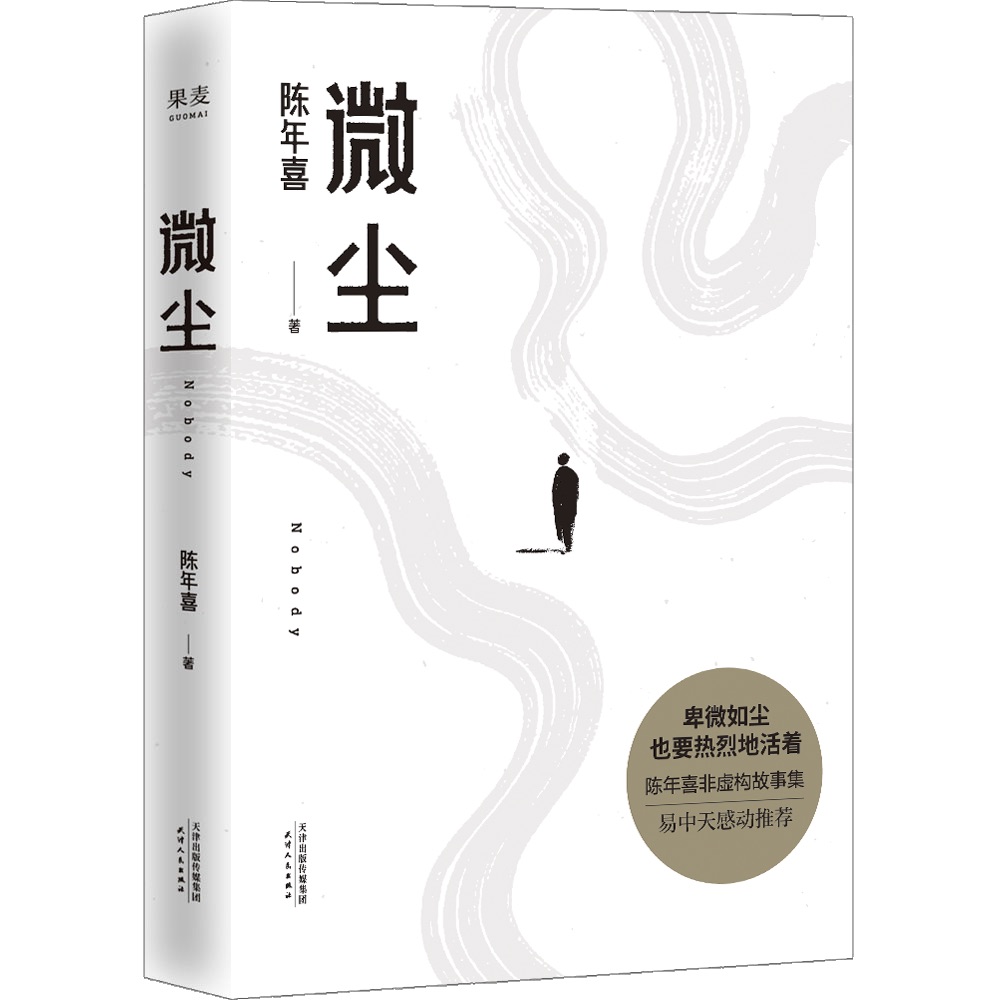
《微尘》
2020年,持续咳嗽的陈年喜被确诊尘肺病。回到故乡丹凤县峦庄镇后,他开始了专职写作的生活。这位曾经的爆破手,一边售卖家乡药材补贴家用,同时用文字构筑着另一个世界。陈年喜的写作语言不事雕琢,叙事方式质朴,却因直面生活的坚硬质地而独具力量。
有读者说,在他的文字里“读到了生活,读到了自己,读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中国社会”。陈年喜自己则说:“我始终觉得我还没有做到,就是让更多⼈去知道,我们这样⼀个群体,这样⼀种⽣活,这样⼀种命运。”
近日,其非虚构题材《人间旅馆》正式出版,封面新闻记者就此专访陈年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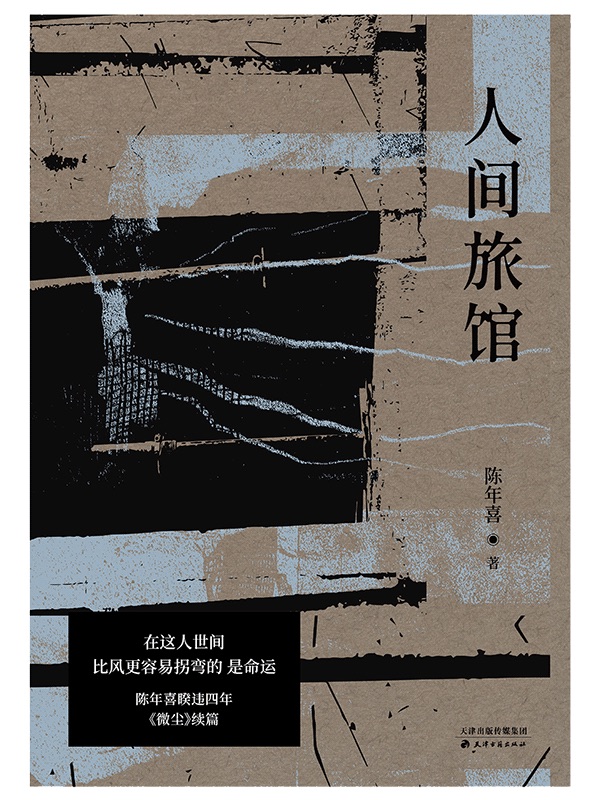
《人间旅馆》
1
尘肺与笔墨的双重呼吸:
在人间旅馆书写生命的回响
许多读者对诗人陈年喜的认识,是从诗集《炸裂志》开始。陈年喜用153首诗歌,浓缩了一位创作者与劳动者对于尘世的思索。在诗歌之外,陈年喜的另一个主要创作领域就是非虚构。《微尘》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与最新出版的《人间旅馆》都是非虚构题材。
在由果麦文化联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作《人间旅馆》中,陈年喜将笔触延伸至更广阔的劳动者群像。全书十九篇散文,以旅馆为隐喻,串联起矿工、马夫、淘金客等“大地上的漂泊者”。矿⼯、背⽔客、烧炭⼯、南阳⼩贩、县剧团⽼⽣、印匠⽼焦、冯琴师、刘唢呐……譬如:计划去喀喇昆仑山找玉的人,他们带着干粮和帐篷,沿叶尔羌河往上走,据说翻过山就是阿富汗;在山脚的岩石上打孔的工人,用炸药炸出一条便路。全书没有⼤起⼤落的情感纠葛,也没有激烈的⽣死搏⽃,⽽是描绘了这些与我们⼀样的普通⼈,为了⽣计四处奔波,寻找那条“活路”的故事。恰恰是这些⽆名之辈的⽣活和命运,令⼈想要似他们那般努⼒纯粹地活,脚踏实地地活。
在自序中,他自陈“我这半生,与漂泊有关……作为行走求生计的人,几十年来以及今天,我总是在和旅馆打着交道,进矿前,下山后,所有来来去去的赶赴中。”旅馆是他串起漂泊生活的载体,也是一个远行人相逢的中介。在《深山旅店》一章,工头与工友的对话堪称经典:“这是上天,哪是上山。”“不行,路上力气都耗光了,到了地方也干不动活儿了。”“那就找个人,帮我们背脚。”
在另外一篇他写道,“为了防⽌落⽯头,井⼝加了盖板。关了井盖,我们就完全陷在了⿊暗⾥,得靠头灯的光亮。每次下井时,我都会告诉井⼝值守的四川⼥⼈别关井盖,我们在下⾯很难受。开始她不敢违章,她说,有啥难受的,不都是那样⼲活⼉吗?我说不⼀样,有天没天不⼀样。我们⼲⼀阵⼦活⼉,就抬头看看天空,有时有云飘过,有时有⻦⻜过,更多时候什么也没有,就那样⼲⼲地蓝着。但就会觉得还有东西在和我们做伴⼉,孤独和害怕就少⼀些。”
2
对话陈年喜:
希望工友们看到,原来我们这样生活过

陈年喜
封面新闻:这本书名为“人间旅馆”。这个书名承载着怎样的隐喻?“旅馆”通常意味着短暂的停留,而您笔下的角色大多在命运中辗转漂泊。您是否想借此表达现代人的某种生存状态?
陈年喜:书名为《人间旅馆》,基于两重因素,一方面我和我的同伴们在生活工作的辗转中,与无数的旅馆发生过联系。另一方面,当下人的生活与命运和无可依身的旅人极其相似,而当下的世界就是一个大旅馆,每个人都在其中暂留和出发,奔波,动荡。这是时代与其中每个个体的宿命。
封面新闻:与之前的作品(如《炸裂志》《微尘》)相比,有何新的思考?相较于《炸裂志》《微尘》等前作,《人间旅馆》在题材、风格或情感表达上有哪些新的探索?
陈年喜:《人间旅馆》以旅馆这一具体又隐喻的事物为载体,描写了一群生活儿女的生活和命运故事,主题和故事场景更集中或者说更关联一些,显得不那么散,但时间和地理的跨度更大一些,有矿山,有故乡峡河,有当下,有更遥远的时光。写作上更平和,语言和感情尽量淡然、原生,不再那么激烈,情感喷张,这也是生活本身的情状,其实,文学即生活本身。
封面新闻:书中收录的19篇故事题材跨度很大(矿工、淘金客、唢呐师傅等),您是如何搜集和提炼他们的故事?
陈年喜:对于我来说,只要挖掘记忆库就可以了,他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身边,至少,这些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。我要做的事就是淡化处理,写出自己的感受。文学的本质是感受,你的感受就是你的世界,就是你的三观。
封面新闻:写作过程中,哪个故事让您最难落笔?为什么?
陈年喜:毛子的故事吧,这个故事在我心里存放了近二十年,我不忍心写出他。他像他的藏宝图一样,安静隐秘。
“写作只是生活的副业”
封面新闻: 您的语言以粗粝、冷峻著称,但《人间旅馆》中也有细腻的抒情。这种风格变化是刻意为之,还是自然流露?您如何看待“苦难叙事”中的诗意?
陈年喜:世界和生活永远需要诗意,苦难本身就充满了诗意,诗意并不只是风花雪月,它包含着悲壮,血泪,平凡。我无意表达诗意,诗意在生命深处,世界自带诗意。
封面新闻:从矿工、爆破工到作家,这种身份转变对您的写作视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如今回望过去的经历,心态是否有新的变化?
陈年喜:我还是一直以在场者的视角来审视和写作,本身我也没有离场,只是生活有些转型。也许是年岁增长,心态变得平和一些,与生活和解了。
封面新闻:最近写作状态如何?写诗方面有什么新的灵感吗?
陈年喜:已经很少写诗了,一方面无话可说,一方面诗歌很难挣到稿费。但我时时还有写诗的冲动,有关于诗歌的思量。
封面新闻:您最近的生活状态如何?跟此前的矿工工友还有联系的吗?如果有工友读到您的书,您希望他们从中得到什么?
陈年喜:我慵懒地生活着,很少参与到别人的生活中。工友们联系得越来越少,不知道他们读不读我的书,我当然希望他们找到慰藉,原来我们这样生活过,并被人看见。
封面新闻:您现在的生活节奏是怎样的?写作是否已成为日常的一部分?您的颈椎手术对写作是否有影响?如何调整身体与创作的关系?
陈年喜:影响很大,我基本不能趴着写作,我一般用手机写作,以减轻颈椎压力。我写作量很小,偶尔写作,或者说被动写作。写作只是生活的副业。
封面新闻:如果有机会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,您会说什么?
陈年喜:生命无悔。
(本文图片由出版方提供)
众和策略-众和策略官网-浙江配资网-专业实盘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大全构建“算力、算法、算据、算用”全产业链体系
- 下一篇:没有了